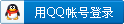驅車武安,幾分鐘就可以看到一座鋼鐵廠;行走武安,每遇到7個人中,就有一個從事著鋼鐵相關行業。
產能過剩,行情下滑,減產停產……在整個鋼鐵行業走進低谷的背景下,這個被一座又一座鋼鐵廠連接起來的城市,連帶生產線上6萬多鋼鐵工人,也正經歷考驗與掙扎。
“鋼鐵世家”的生計變化
沿著武安南環路走下去,無數巨大的煉鋼爐聳立,由鋼筋混凝土構成的廠房錯綜排列,不時有機器轟鳴聲、鋼軌撞擊聲發出。
但在劉方眼里,現在這條街上太“安靜”了。三年前,“即使是半夜,這條路也是燈火通明,都是機器撞擊的聲音,人說話根本聽不到。”
今年不滿30歲的劉方,出身于典型的“鋼鐵世家”,從小就生活在鋼筋混凝土的世界。父親劉剛是其所工作的鋼鐵廠的“開廠元老”,大伯劉文也是這個廠的“元老”之一,大舅哥劉奇在武安另一個鋼鐵廠工作也快10年了。
他說,“這個廠大概有三四千人,都是這個村里的人,當初是集資建廠,我們家出了一萬多吧,還有的家里條件不好的,出了幾百塊錢也可以到廠里工作。”
因為鋼鐵行情好,父親劉剛所在鋼鐵廠對鋼鐵工人有很好的福利,凡是家中有上學的學生,一年會給1200塊錢補助,“我上的專科,給我補助了三年。”
大學同學羨慕他,都稱他為“鋼鐵二代”。
2005年從石家莊畢業時,他父親想要他回武安鋼鐵廠工作。但劉方以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為由,拒絕了父親的好意。他被分配到山西呂梁的一個煤礦項目部做后勤聯系。“一個月工資三四千元,那個時候行情好,不管是煤礦還是鋼鐵,打個電話就能銷售了。”
不過,被困在偏僻的大山里,二十出頭的他還是覺得“很孤獨”。兩年后,他回到武安,投身于父輩奮斗中的鋼鐵熱潮中。他如今的妻子,早于他一年就回到武安進入鋼鐵廠工作。
就在這一年,武安市的GDP達到343億元,財政收入42.2億元,并且發展勢頭仍然強勁。武安人僅用5年時間就使這座城市得以迅猛發展,用當地一位出租司機的話說,“武安的鐵礦每天都能掙一輛奧迪,鋼鐵廠每年都在批量生產千萬、億萬富翁”。
“當時是小高爐,后來就慢慢增加,我回來時候,我們廠有了年產能300萬噸的高爐,那時候在武安屬于先進了。”劉方說。
大學期間學醫的他,進入鋼廠后做起了安全員,每個月工資有四千左右,最多的時候拿過六千多,加上各種福利分紅,一個月也能賺個小一萬元。這份監管安全的工作,也給了劉方滿滿的安全感。
2012年,工廠效益達到了頂峰。劉方選擇在這一年與相戀3年的愛人結婚,他們很快有了小孩。賺了錢,他要在武安市區買套房子。“不管住不住,這是面子問題吧。”他說,由于還沒有充裕的存款,他們以按揭的方式在武安市區購置了一套房子。
一家人其樂融融,但變化很快就到來了。由于產能嚴重過剩,2012年鋼價急轉直下,一氣兒跌回上世紀90年代水平,賣到了“白菜價”。劉方一家真實感受到凜凜寒意。起初對工作的那種安全感,也被各種擔憂與無奈的情緒替代。
“現在工資最起碼降了百分之十,并且沒有任何分紅。”劉方苦笑道,“我現在一月能拿到三千多,媳婦是兩千多,還要養孩子,還要還貸款。”
現在,他和妻子在經濟上難以完全不依靠父母。而他父親劉剛的情況還不如他,“他所在工作組已經調休,每天工廠會發些補助,但那些錢也只夠吃飯了。”
每到吃晚飯時候,他們一家從沒像現在這樣人員齊整,“錢省著只是夠生存,不能出去花,出去玩肯定玩不起。”一家人已經養成習慣,每天圍在一起看新聞聯播,總盼著能從新聞里看到某些鋼鐵的利好,他們說的最多的,也是鋼鐵廠的效益。
父親劉剛現在最常說的就是,讓他長點本事,走出這個圈。因為心里著急,劉方賣過麻辣燙,賣過水果,但是都沒掙到錢。他身邊的朋友多少也都在謀劃著出路,甚至有的跑去山上抓蝎子,但也只能賺點零花錢。
對如今持續低迷的鋼鐵行情,劉方很掙扎,“現在除了工資不漲,什么都漲了。又碰上特殊時期,壓力真的大了,就特別想干別的了。”
一代工人的轉型與擔心
與兒子的掙扎相比,劉剛對鋼鐵的感情更純粹。從建廠到現在,從黑發到白頭,劉剛陪著這個廠走過了20年。
他見證了鋼鐵業曾經的繁榮。前些年鋼材市場需求旺盛、利潤豐厚,民間資本紛紛涉足鋼鐵,導致鋼鐵產能迅速擴張。多名鋼鐵企業負責人用很多形象語言描述鋼鐵行業最紅火的年代:“投資兩條生產線,掙錢像用耙子摟一樣”“一座鋼廠就是一臺印鈔機,日進斗金”“遷安的鋼鐵廠老板用麻袋裝錢一口氣買十幾輛奔馳”……直到現在,武安的首富仍然是鋼鐵廠老板。
他也見證了鋼鐵業如今的困窘。從2010年開始,鋼鐵行業真正走入下行通道,鋼材價格一路下跌。同時,噸鋼利潤也大幅下滑,有人形容“最早一噸鋼能賺一部手機,后來能賺二斤豬肉,到2013年上半年只能賺一瓶礦泉水。”
劉剛所在崗位是煉鐵的鑄床,“整天和1500℃以上的鐵水打交道,人工甩鐵”。他每天在沸騰著的鐵水罐旁干活,鐵水猶如翻滾的巖漿,鐵花不時向周圍噴濺。煉鋼,在所有的工種當中是最危險的一種,稍一閃神,火花就砸出來了,“一塊紅鐵崩到身上,跟子彈是一樣一樣的,可能致殘,甚至沒命。”
這樣高危的工作性質,也讓劉剛深感自己身上責任重大,二十多年來,時時提醒自己站好每一班崗。煉鋼,早已在劉剛心里烙下了印記。
現在,由于工廠要控制成本,會采取檢修輪休制度,關停一部分設備,給工人放假,另一部分無事可做的工人負責檢修設備。
突如其來的閑適,讓看慣沸騰鐵水的劉剛很不適應。雖然暫停生產,但仍然每天跑去廠里溜達一圈,看著關停的設備和靜默的廠房,他會不自覺的嘆息幾句。碰上熟人,也會停下來聊上幾句,雖然都是無關痛癢的對話,但是看著彼此熟絡的人都還在,看著廠房的大門仍然開著,他的心里總也會寬慰些。
也有些人去干臨時工掙點零花錢的,但大部分人都在等這個廠好起來。
“都在往好的方面想吧,這么多人呢,不會說倒閉就倒閉吧。”很多時候,他更像是在自問自答,并不真的關心提的是什么問題。也許他只是不敢去想:萬一真的倒閉了,他該去哪兒呢?
劉方把父親的失落看在眼里,他深深地感受到內心的那種無力感,“像我們這輩的人還出過遠門,像我父親最多也就去過省城,他們真的不知道干什么。”
劉剛文化水平不高,但對保爾·柯察金,他特別熟悉。說起《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他一下來了勁,“奧斯特洛夫斯基曾說,‘鋼是在烈火與驟冷中鑄造而成的。只有這樣它才能成為堅硬的鋼,什么都不懼怕。’我們這一代人也是在這樣的斗爭中、在艱苦的考驗中鍛煉出來的,并且學會了在生活面前不頹廢。”
可現實是,我國鋼鐵產量經過十多年的爆發式增長,鋼鐵行業普遍出現產能過剩現象,產業亟待調整升級。很多專家都預言,鋼鐵行業拐點開始顯現,中國鋼鐵行業也將迎來兼并重組的機會,“大魚吃小魚”的現象將不斷上演。
武安市市長魏雪生介紹說,“武安市16家鋼企中有4家屬于一類企業,盈利狀況較好,其他都不同程度遇到各種困難,有的勉強維持生產,有的隨時有倒閉的風險。為了壓減和升級產能,到2017年底,要完成整合4至5家大型鋼鐵企業。”
像劉剛這樣的老一代鋼鐵工人,由于對新技術變革反應的滯后,雖然他們在生活面前永遠都不頹廢,但仍很可能在行業重塑的過程中就此退出歷史舞臺。
眼前的老杜長得白胖,臉上雖然無表情,卻也總像在微笑一般。用他自己的話講,“這就好像生活給我的一個玩笑。”
老杜開得一手好車,在鋼鐵廠做司機快兩年了,但他并不是這個鋼鐵廠的正式員工,“就是過來養老來了。”
據他講,10年前,他看好鋼鐵的行情,將家里的積蓄全部用在買大貨車上,那時候,他自己開一輛,雇人開一輛,每天往返于各鋼鐵廠周邊,拉送鋼鐵生產剩下的廢棄邊角料,不到一年,便將當初買車的錢賺了回來,并由此賺得人生的“小金礦”。
“原來效益好的時候,都是用車拉原料,運產品,只要有東西就能賣掉,每天都能掙錢,自己找材料,自己賣。”
在鋼鐵行業嘗到甜頭的他,并沒有乘勢擴大自己的商業版圖,而是選擇了“穩妥”,將自己的兒子和兒媳婦都安排在了鋼鐵廠,算是解決了自己的后顧之憂。
但好景不長,從前年開始,鋼鐵行業的頹勢已經顯現,由于市場不景氣,加上自己的謹慎錯過了轉型的好時機,老杜眼見著自己拉一車料賠一車錢,就索性把車都給賣了,自己回到鋼鐵廠打了份臨時工,當起了司機。
這兩年,鋼鐵形勢持續惡化讓老杜的笑容不再多見,但是更多的,他在為兒子兒媳發愁,“兩個人都是剛成家,但是現在市場不景氣,總是擔心他們失業。”
對“鋼鐵工人”身份的認同感
鋼鐵市場形勢嚴峻,但剛性需求依然存在,一些鋼企對市場好轉還抱有希望,沒有選擇停產。停產可能損失更大,一座450立方米高爐,一關一開就損失1500萬元。
武安市工信局負責人分析,“鋼鐵在未來10到20年,應該還是基礎產業,這種局面不會變,鋼鐵企業不會全死掉。鋼鐵企業的問題,出在技術和設備,要不斷自我創新和升級,圍繞這些問題解決。”
然而,給鋼鐵企業帶上緊箍的,不只是行業寒冬,還有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之間的矛盾沖突。
黃源清也是第一代鋼鐵工人,當年他參加工作時只有18歲,“那時候,別提了,我在運輸部開火車頭,礦石、焦炭等原料順鐵路線運來后,我們再配送到各貨位。一天下來渾身全是煤塵,臉黑得家里人都認不出來。”
環境的惡劣一直持續了很長一個時期。黃源清有深刻印象,“以前的鋼鐵廠,高爐外圍的空氣全是黑的,都看不見人。”
黃源清剛到鋼鐵廠時,分至工長崗位,要時常到操作一線,“粉塵對肺不好,飄出來的炭灰落在脖子上都是亮晶晶的,黑得發亮。”
很多鋼鐵工廠的生產方式依舊是粗放式的,要想排放達標,必須上脫硫、除塵設備,可動輒六七千萬元的投資,讓這些搖搖欲墜的企業無法承受。隨著破碎錘砸下的聲聲悶響,無數條落后的生產線在河北省化解鋼鐵過剩產能集中行動中被拆除,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
鋼鐵廠區不再整日被灰暗的天空籠罩,地面也潔凈了許多。“現在國家有強硬的指標要求,讓你節能,讓你降耗,讓你環保。”黃源清如今仍留守在工廠工作,但國家對環保的重視,讓他明顯感覺到,就像突然之間,一切有了巨變,“以前環境不好,粉塵多,附近村民就舉報,老來提意見,現在情況好多了。”
陳明是煉鐵廠一個高爐車間的副主任,來到工廠的11年里,他切身感受到了高爐“大型化”、人員“縮減化”的過程。“我剛來時爐子是1260立方米,車間要有160多人輪班,現在是3200立方米,人反而減少了,只有80多人輪班。”
陳明自豪地向我們描述起來,當時一天產鐵2500噸,現在將近8000噸,“我們就這么點兒人能產這么多。”
不過,陳明也不無擔憂,“對我們來說,今年確實是最困難的一年,但是不管怎樣,工廠還在發給我工資,那我就堅守好自己的崗位,對得起自己,也算對得起廠里發給我的工資了。”
鋼廠工人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工作不再臟和苦,他們依然認同自己作為“鋼鐵工人”那種特殊的身份。
下午4點,李亮準時趕來接班。1990年生的他是冷軋廠酸鍍車間鍍鋅線的工人,2013年大學畢業后進入鋼鐵廠工作。
“我是學化工的。現在國內還沒有鍍鋅這個專業,我學的算是離這個很近了。鋅是化學元素嘛,配成溶液往板子上打,保證它不會腐蝕。”李亮對我們說起自己的工作時,頗為自豪,因為他所在的生產線是國內第一條熱軋薄板酸洗鍍鋅生產線,這條生產線主要是用鹽酸將氧化鐵皮去除,然后在鋼材表面鍍鋅防止氧化,“這樣的工序能將鋼材保存20年不生銹”。
“以前,我沒想到自己會做個鋼鐵工人,我也以為鋼鐵工人都是渾身臟兮兮的,黝黑的手、黑紅的臉,特別特別辛苦”。李亮說,“現在你們看我,我干完一天活也挺干凈的。”
父母都從事鋼鐵相關行業,或多或少會影響到李亮的選擇,“家人很支持我的工作,認為年輕人需要歷練。雖然鋼鐵形勢不好,但是我覺得大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團結了,做好自己的,工廠就會更好。”
像李亮這樣的80后、90后高學歷技術工人,還有很多。他們平時打扮時尚,而一旦換上工作服,對工作的專注與尊重絲毫未變。
他們去哪兒?
作為鋼鐵產能最大的省份,河北分配到的任務是截至2017年底,壓減粗鋼產能6000萬噸。
任務分解到武安。2014年2月,武安拆除6家企業的8座高爐。市人社局局長尹長興說,這涉及7110名職工轉崗或失業,相關上下游產業加起來2萬多人。“這個人數還僅是初步摸底的數字,最后肯定比這個數字大。”
后鋼鐵時代,工人們或主動或被動置身這場變革,都在發問:我們去哪兒?
武安的資本就在于資源豐富,僅鐵礦石儲量就達5.5億噸,是全國四大富礦基地之一,郭沫若有詩贊曰“武安鐵礦峰峰煤”。過往20年間,鋼鐵給這座小城帶來巨額經濟收益,創造了數萬人的就業,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一部分民營鋼廠如今在環保壓力下,相繼關停。
楊自茹今年32歲,是武安一家民營鋼鐵公司的天車工,公司自2014年7月份就已經解散,幾百人全部自謀生路。本來按照合同,楊自茹是2015年3月份才到期,但公司從去年5月份就發不出工資了,保險更是已經拖了兩三年,現在已經開始變賣資產籌錢還賬。
楊自茹說,之前自己和丈夫都有工作,每個月還能攢點錢,現在只剩丈夫一個人工作,每月基本就剩不下了。“公司效益最好的時候,廢料里面的鋼渣每公斤都賣1塊錢,現在好鋼才9毛錢。”她顯得失落而留戀。
楊自茹目前仍在家待業,不知道自己除了在鋼廠工作還能做什么,“在鋼廠做了這么多年,也不會干其他的工作啊。”
據報道,《河北省鋼鐵產業結構調整方案》(下稱方案)正在進行論證。在人員安置問題上,方案要求化解過剩產能企業研究制定并落實職工安置方案,報企業所在地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確保職工安置政策、資金、服務到位。并要求,企業一次性、大批量裁員的,要事先向當地政府報告。
河北各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被要求加強失業動態監測和就業形勢分析預測,將化解產能過剩矛盾中失業人員納入就業扶持政策體系,并且要求做好失業人員社會保險關系接續和轉移,按規定落實好其社會保險待遇。
打電話給趙謙時,他正在自己的養雞場核實公司新的訂單。趙謙今年三十歲出頭,2014年9月從鋼鐵廠離職,離職的時候他已經工作了4年,辭職原因是“賺得太少”。
由于家里有養殖經驗,他從親屬那里籌集一部分資金,加上自己工作幾年的積蓄,在老家附近辦起了養雞場。他說他們原來廠里11個人的組已經走了三四個了,不過都是自己主動辭職的。趙謙說他們都是勞務用工,也就是俗稱的“臨時工”,一般月工資稅后大概兩千六七百元。
離職前的半年時間里,趙謙明顯覺得,鋼鐵行業確實今不如昔了,他說,2008年鋼鐵正火那會兒,拉鋼材跑運輸的人,“一個月就能賺一輛20來萬元的小車,再一個月小車就能換輛大車”,現在,“能保本就不錯”,趙謙扳著手指頭算了筆賬,“一個司機一月就得5000塊,再加上油錢、保養費、修車費各種費用,可不也就是保本”。
所以,他當初才下決心與鋼鐵決絕。可喜的是,因為主打生態招牌,現在人對養生愈加重視,他公司的訂單一直不斷,用他自己的話說,“發展挺好的,算是徹底改了行,擺脫了沉重的鋼鐵業。”